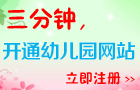北京协和医院教授呼吁理性保胎
今天你保胎了吗
根据15%~20%的流产率,2007年,中国约有300万名孕妇流产。这一数字,相当于三个河南省的年新生儿出生数。一个年均接诊14000人次的生殖医生,给我们讲述北京妇女怀孕早期保胎的真实情况。
300万流产孕妇
邓成艳的诊疗室外已经等了50多人。她的小房间很不好找,这是全院最老旧的一栋楼的半地下室。七弯八绕,看了很多指示牌,才找到迷宫的中心——北京市协和医院生殖中心。这些人大都是女性,有的小腹微隆,有的一旁有沉默的男伴,或站或坐地塞满走廊,心急的不时往门里面张望。
“大部分是来看不孕的,还有保胎的。”2009年1月3日,协和医院门诊部放假,邓成艳穿得休闲,斜靠在椅背上,一边说一边往门外比划,仿佛外面随时会突然走进来一个病人。“都是希望要孩子的。”邓成艳笑说。
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教授邓成艳,一周9个门诊,年均接诊14000人次,包括不孕病人与妊娠早期先兆流产患者。在邓成艳接手的保胎病人中,大部分是孕早期(妊娠前三个月)就来看病的。她们的病情相对简单,最终结果在一开始就能预计得八九不离十——要么是孩子有问题,基本保不住;要么是孕妇自身孕激素水平低下,但孩子是好的,通过人工干预补充就差不多能保住。
“怀孩子就像种庄稼,地再好,肥再足,种子有问题,也是长不好的。”对前来要求保胎的病人,邓成艳总是拿种子和地的例子来说明,这样沟通起来容易很多。
回忆起种子不好的病例,邓成艳能说出一箩筐。一位名叫白礼慧的孕妇,今年已经34岁,前两次怀孕均以胎儿停止发育告终,没有查具体的原因。第三次怀孕了,孕激素依然偏低,这次她找到邓成艳。人工补充黄体酮,孕8周B超显示胎儿依然没有胎心胎芽,白礼慧第三次遭遇胎儿停育。
“这对孕妇们是很大的打击。”邓成艳说,B超结果出来,很多孕妇当时就在B超室里泪如雨下。邓成艳给白礼慧做了刮宫和绒毛染色体检查,结果显示:白礼慧腹中胎儿是三倍体染色体畸形,此类基本都胎死宫内。
通俗地说,孩子能不能保住主要分两种,第一种是品种好,但确实缺乏营养;第二种是品种不好,不是好孩子,要被大自然淘汰掉。“流产的发生率约占全部妊娠的15%~20%。”邓成艳说,近3年中,她所在的生殖中心对接诊的222例次有完整病历的保胎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统计出这一结果。这一数据与国外的数据一致。
根据卫生部发布的《2008中国卫生统计年鉴》,2007年,中国活产胎儿12506498名,按照15%~20%的流产率,2007年,我国有约300万名孕妇流产。这一数字,相当于三个河南省的年新生儿出生数。
在这些流产的案例中,七到八成是孩子自身有问题,而被人体自然淘汰掉。这意味着一百名胎儿中,有15名胎儿以上会因自身缺陷而进入优胜劣汰的“淘汰环节”,并最终被流产。这些不幸流产的孕妇们如果去做绒毛染色体检查,将有至少一半人可以检查出流产胎儿的染色体缺陷。
现代医学对人体的了解仅30%左右,邓成艳仍不免赞叹人体自身的完美进化——如果胎儿是不好的,它会给大脑传达一种信号:“种子不好,要流掉。”这种信号一旦启动,孕妇体内本来正常的孕、雌激素就会直线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外界再怎么补充孕激素也无济于事,体内孕激素水平依然无法达到正常值。少了激素调节的胎儿就开始变得没有营养,“坏种子”最终在营养不良中死去,淘汰了。
问题是,一些孕妇的孕激素水平从一开始就偏低,这令人格外紧张,且充满期待——也许只是孕妇自身的激素分泌过低罢了。这样的事情发生在邓成艳同事的女儿身上。医院同事的女儿一开始就孕酮偏低,还出现相应的下体出血的先兆流产症状,她要求药物保胎。
“我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如果种子是好的,我就会给你保好的,种子的营养问题包在我身上;但如果种子有问题,是没有办法的。”邓成艳说。在保胎的过程中,邓成艳全力以赴,孕7周,B超有胎心搏动了。每两周监测雌激素和孕激素水平,一直在缓慢上升。过了妊娠12周,准备转产科,突然两类激素水平下降,马上B超检查,胎儿已长3厘米,但胎心消失了。染色体检测结果发现多了一条第18号染色体,“种子”确实是有问题的。
还有一种流产,既不是“种子”不好,也不是孕妇孕激素分泌不足,而是刮宫次数过多。由于个体差异,有些人刮宫七八次照怀不误,有些人刮一次,子宫内膜就刮伤了。“就相当于在盐碱地上种庄稼,根本没法扎根,所以一有就流产。”邓成艳打比方说。刮宫次数过多也是早期流产的原因——“土地”一旦被破坏,“种子”无处落脚,给足孕酮也没用。
从另一角度看,流产值得庆幸,是优生优育、大自然的淘汰过程。但是,对那些受孕困难或者有过不良孕史的人来说,怀孕机会分外珍贵,保胎则成了全部生活的重心。这时候,医生唯一可做的只是给“种子”施肥。如果“种子”是好的,他们大都能安全地降生到这世间。
保还是不保?
“孕酮多了并没有什么害处,有些孕妇就要求医生注射,图心安。”邓成艳说。去她那里要求保胎的通常是有过不良孕史(比如流产史),或好不容易怀上的。对于这些孕妇,邓成艳的态度很明确:要检查。是不是缺?缺多少?缺多少补多少。
“本应该被淘汰的畸形胎儿,有可能经过保胎而得以存活,直至较大孕周才被发现。”协和生殖中心的七年调查结果显示,222例次保胎病例中有2例畸形,一例在怀孕27周发现唇腭裂,引产了。另一例足月分娩,发现6指、外生殖器畸形及食管气管瘘等多发畸形。
保胎后出生畸形率为9.0‰,没有超过国内新生儿出生缺陷率13.7‰。尽管保胎不增加出生缺陷的风险,但在现今紧张的医患关系下,面对前来要求保胎的病人,邓成艳在正式治疗前,都会告诉她们相应的风险,征得对方同意,并签订相关协议,方才动手。
现实总爱开更复杂的玩笑。2008年3月,已停经三个月的刘羽洁挂上邓成艳的号。正常情况下,怀孕7周一定能显示胎心,而B超显示,刘羽洁的腹中只能看到一个胎囊,没有胎心。本来,如果胎儿正常发育,三个月的胎儿就已经成形。
在刘羽洁之前的检查中,医生都认为胎儿停育,建议刮宫流产。幸运的是,刘羽洁记录了自己的基础体温。根据她出示的体温表,邓成艳重新分析,发现她只相当于怀孕35天,而35天只有一个胎囊是很正常的。
“她孕酮低而且有点出血,我跟她说明了可能的风险,问她愿意不愿意保胎,她愿意,我就给她保了。”邓成艳回忆说。
谁知第二天就出事了。这天上午,邓成艳正在看门诊,门口突然窜出一位老太太,指着邓成艳就嚷嚷开:“你说,到底孩子是不是好的,为什么有的大夫要清宫,有的要保胎?”这一吵就是十几分钟,差一点就引来医院的保安。邓成艳没办法,只得拿出和刘羽洁签订的协议,指着签名告诉老太太:孩子是孕妇同意要保的,风险也是一开始就说明白的。孕7周B超发现胎心跳动,刘羽洁笑着说,婆婆不好意思进来。现在大胖孙子已经抱在手。
是好孩子还是坏孩子?保还是不保?这一切在孕早期,都是个谜。当前的监测手段难以很快判断早期胎儿是否正常,但可以迅速测出孕妇体内的相关激素水平,因此,对于自身功能缺陷、有胚胎停育史或先兆流产史的患者,以及不育史、受孕困难的患者,由于胎儿珍贵,一旦确定妊娠,生殖中心采取的主要措施仍是积极监测观察。
但有一个原则,邓成艳始终坚持并再三强调:雌孕激素水平正常,就不需要补充。因为黄体酮注射液一支才7毛8,加上注射费也才1块5一针,注射多了对胎儿无害,因此被广泛应用。有的医生不查孕激素水平,就给病人打一点或者口服黄体酮,孕妇也乐得心安。
“凡事都有利弊,就算无害,至少屁股疼啊!”邓成艳说,黄体酮的注射很疼,而另一些口服雌激素也或多或少有价高、患者不耐受、头晕嗜睡等缺点,因而并非用了都好。与其每天跑医院打针,提心吊胆还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否需要保胎,不如一次检查确认,更加心安,也大大减小心理压力。
如果以绒毛膜促性腺激素水平衡量妊娠,实际总胚胎流产率可达31%。早期流产中,半数以上是由于染色体异常。另外,环境因素、有害药物、病毒细菌及放射性物质等均可导致胎儿畸形和流产。
“不停,我就不停”
2009年1月2日,石景山医院妇产科,预产期已过四天的孕妇郭艳红在病房里来回踱步,沉默不语。三天前,郭艳红就有了轻微的宫缩、出血等临产征兆,但三天之后孩子还是没生出来。“都怪我怀孕时在家里一直坐着搓麻将。”终于停下脚步,郭艳红半开玩笑地认为是缺乏运动才导致了今天的不顺利。
郭艳红怀孕四十多天,突然腹痛,到医院打了几针黄体酮,进行保胎治疗。四个月后,郭艳红便辞掉文员工作,转职“保胎员”。“上网也少了,怕电脑辐射影响孩子。”遇到问题,比如孕妇该吃什么做什么,她还是会上网查一下。
工作压力并不是最主要的问题。“太远了,每天要坐公交车一个多小时上班,挤来挤去对孩子不好。”26岁的郭艳红和丈夫商量后,辞去原本收入不错的工作,小两口开始靠着丈夫每月3000元收入过活,“肯定会拮据一点,尤其马上又要多一张嘴。”
郭艳红觉得日子可能会困难一点,但孩子是最重要的,孩子出生后的一两年也没有出去工作的打算。她说以前的公司同事中,像她这样的“专职保胎员”并不少见。
“这的确很时髦。”邓成艳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有些孕妇从怀孕前就开始补充叶酸和各种维生素,比较时髦也比较费钱。在前来就诊的孕妇中,约有一半人是因为自己恐慌来要求保胎。其中有过不愉快孕史的可以理解,而首次怀孕因为恐惧就要求保胎是不值得提倡的。
有些孕妇觉得黄体酮不安全,认为会造成女性胎儿的男性化。对此,邓成艳也作出承诺:这是误传。在邓成艳看来,病人也有两种极端,一种认为不能用一切的药物,怕对胎儿产生影响;另一种则是没问题也要用药保胎,图安心。
这两种情况,在当下的白领一族中都表现得格外明显。她们工作压力大、生育年龄也偏大,并具有一定经济条件,对孩子的期望值也格外高。据有关部门调查,北京市平均生育年龄5年提高1岁半,早在2005年就近29岁了。与此同时,她们还喜欢刨根问底,似懂非懂,互相问,不太相信医生,“你为什么要给我这么做呢?黄体酮会不会造成女性胎儿男性化呢?如果保,会不会保出畸形?”在邓成艳的接诊中,这样的问题常常连珠炮似的袭来。
经济条件较好的孕妇们往往会挂邓成艳的特需门诊号,一个号三百块钱。何怡已经流产三次,第四次怀孕后,她一直定期看邓成艳的特需门诊。一开始,何怡的孕激素水平偏低,邓成艳用孕酮帮她保到13周,何怡体内的孕激素水平已经很稳定,邓成艳准备给她停药。
结果她说“不停,我就不停。”邓成艳一边笑,一边轻轻摇头,何怡一再坚持继续用药,这令邓成艳颇为为难,“我觉得没必要开药,就不开了,最后只能对她说,你要吃就到别的地方开去。”
类似的恐慌还表现在产检上,有的孕妇自从怀孕,每两周就会来医院查体一次。“除非你特别想要这个孩子,想倾尽一切保住,一般不推荐。没有问题干吗要一趟一趟跑医院啊?”邓成艳说。
保胎方面的费用,邓成艳也算了一笔账。检查一项激素45元,三项相关激素全检查也才135元。这固然比1块5毛一次的孕酮注射费高了许多,但与天天跑医院扎针、提心吊胆又承受悬而未知的压力相比,无疑是更好的选择。“查一下没问题就不用打针了,很多孕妇心情也非常愉快就回家了。对这些孕妇来说,好心情比什么保胎药都管用。”邓成艳一字一句地说。
医生的建议
邓成艳反对盲目保胎,同时也表示,妇女的三期很重要:月经期、妊娠期、哺乳期,都是抵抗力比较弱的时候。国家要求重视妇女三期的保健,其中妊娠期的休息非常重要。孕妇是否需要停职保胎不能一概而论,比如从事公交售票、化工原料有关职业的孕妇都不适合工作了。对于一般白领,上班坐办公室用电脑是没关系的。
对于网络上卖得火爆的孕期防辐射服,邓成艳不置可否:“防辐射服是否真的能够使流产率、畸形率之类的数据有所下降,我没有一手资料,不能评价,不推荐也不反对。”
对于保胎,邓成艳有她的两条建议:首要的就是什么年龄干什么年龄的事。不要因为工作耽误了要孩子的年龄,鱼与熊掌难以兼得。如果实在错过了,则尽量放松,毕竟需要保胎的只是小部分人。
尽管邓成艳这样的医生人群对于保胎有着理性的态度,但据卫生部《2008中国卫生统计年鉴》统计,北京和浙江两大发达省市高危产妇比重高达30%以上,这一数字接近全国均值的3倍。
《2008年中国卫生统计提要》也显示,从1990年到2007年,城市医院住院病人中,妊娠病、分娩病及产褥期并发症一直排前十位疾病中的第四位,比重由8%上升到9.96%。在卫生条件相对较差的县医院,这一排名和比重分别攀升到第二位,和17.35%。(为保护个人隐私,文中孕妇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