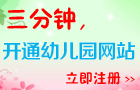她们也不像“外来妹”,有青春有资本对未来充满憧憬。“外来嫂”的青春稍纵即逝,若再苦熬几年,等待她们的也许更是凄风苦雨。但她们是如此的朴实、勤劳而忘我,以至于人们差不多忘了她们也是女人,她们和其他的女人一样有着自己的情感、心理与生理需求。
下面是阿月的自述:
我老家在安徽,来温务工已经三年多了,今年35岁。三年前我是和丈夫一起离乡背井出来打工的,家里还有一双儿女,大的10岁,小的8岁,都在上小学,跟着他们的爷爷奶奶。到了温州,我很快就在一家鞋厂找到了活儿,但丈夫一直找不到他认为合适的工作。
三个月后,在一个朋友的鼓动下,他去了广州,并在那里找到了一份工作,我也曾想跟随他到广州打工,但那里根本没有我立足的地方,靠丈夫一个人的工资,我们没法活,我又只好回到温州。就这样,我们开始了两地分居的生活,至今已整整三年。
一开始还用电话经常联系,但后来感觉话费负担实在太重了,联系就越来越少。来去探亲的路费及旷工的损失更不是我们所能承担的。这三年来,我们只见了三四次面,基本是在过年的时候。我们成了真正的牛郎织女。
丈夫离开以后,孤单就包围了我。白天,我下死劲地干活,就是为了让自己累,累得死去活来,晚上就好入眠。然而,随着时光的流逝,我的焦虑感越来越强,有时候无论怎样累,到了晚上都翻来复去地无法入睡。我住在工厂的宿舍里,同宿舍有三个人,一个已婚,丈夫也在温州,另一个还是小姑娘。
一开始,三个人说说笑笑日子还算好过,但不久,小姑娘开始谈恋爱,经常将在同一个厂干活的男朋友带到宿舍来,宿舍里的气氛就有些变了。再后来,另一个已婚的也将丈夫晚上都留宿在我们这里,他们的甜蜜时时刻刻刺激着我,但为了我们的友谊,我又得装得很开心、很欢迎他们,我内心的苦不知何处去诉。
与丈夫、孩子通电话是我生活中的唯一慰藉,但能通话的时间实在是太少了。我的失眠越来越严重,有时一个晚上睡不上两个小时,白天又要干活,这使我的精神状态越来越差,干活时出的差错也越来越多,老板已经几次严重警告我了,要不是我以前的表现很好,也许已经被炒了鱿鱼。
我们厂里像我这样夫妻分居两地的人不少,也有不少人像我这样异常苦闷无处解脱。有些男的就去一些低档的发廊或卡拉OK厅,找一些“野鸡”解决生理问题,而像我这样的女的就无处可去了。也有一些“光棍”向我暗示,我们可以组成临时夫妻,现在先搭档把日子对付过去,以后真正夫妻团圆了,谁也不干涉谁。我没有答应,因为这样做对不起我的丈夫。
如果我的丈夫在广州也找一个这样的临时“妻子”,我还不如死了呢。而且,这种“临时夫妻”造成的悲剧也是很多的,我的一个女朋友就因为找了一个“临时丈夫”,被在家乡的丈夫知道了,差点酿成血案,我绝对不会去踏这个雷区。
我长得并不难看,厂里的一个工头也对我有“那个意思”,我自然是不会答应他,但当漫漫长夜我难以入眠时,我的内心就在矛盾中煎熬。有时我真想不顾一切地迈出那一步,反正现在开心就行了,管他以后怎么样呢。但以我的道德观念,我是不会真正这样做的,我的理智一次一次地压抑着自己的冲动,直至身心疲惫。
我是一个女人,而女人对情感的需要有时远甚于生理需要。我省吃俭用拼命干活,像一头牛似的,但我的内心是与其他女人一样渴望温情,渴望有人来爱我、疼我的。与丈夫好长时间才通一次电话,短短的几分钟,把要紧事情讲完就赶紧挂机,然后每天日子枯燥地过下去,我觉得自己已经成了机器。
一年前,我受了工伤,不得不休息一段时间,老板还算讲良心,没扣我的工钱。我的一个老乡经常来看望我。他比我小两岁,见我孤身在外生病实在可怜,就常常来为我端个茶递个水什么的。一来二去,我觉得我们之间产生了一种什么东西,这东西非常美好却让我十分有罪恶感。
后来,他到另一个城市去了,走了以后我们基本就没有联系。他刚走那阵子,我觉得我身体里的血与肉全被他抽走了,只剩下一个空的皮架在我的骨头上,每天空落落地飘来飘去。我简直不知道自己是死的还是活的了。
这漫漫岁月实在难熬,我不知道何时是个尽头。出来打工三年多,我和丈夫并没有什么积蓄,拼命干活赚来的几个钱,寄回家给孩子付学费生活费,也就所剩无几了,自己的生活那是非常省的,三年来我几乎没给自己买过新衣服,更别说
化妆品什么的。我和丈夫的理想是要在老家盖一栋新房,再供两个子女上完大学,这个理想的实现是遥遥无期的,而我就在这遥遥无期中耗尽自己的青春和生命。
有时,我觉得自己快要疯了。夜里睡不着时,我觉得自己的身体里有什么东西在撞击着,我整个人差不多要爆炸了,我很想站起来,大喊大叫,到处乱跑,但最终还是被自己苦苦地压抑住了。
有一次,我的那个已婚室友带她丈夫到我们宿舍来,房间里明显留下了他们亲热过的气息,我突然有一种冲动,想冲过去揪住那个女室友的头发,将她毒打一顿。虽然我什么也没做,但我觉得,我总有一天会发疯的,我总有一天会干出自己控制不住的事情,我真的好害怕。
我觉得自己活着简直没有任何的乐趣。一天又一天,我吃喝拉撒让自己活下去,完全是为了两个孩子,我不能让他们没有娘。等到他们大了,我也老了,我不知道我这一生过得有什么意思。
回复:
阿月的遭遇是十分让人同情的。“外来嫂”也是人,她们不应该生活在如此的痛苦中。但是面对现实,我们的同情是这样的无力。我想,像阿月这种境遇的人不会只有一个吧,可以说她是代表着不少在底层挣扎着的外来劳动者的生活。
尽管大多数新温州人已经融入温州,过着与一般温州人一样忙碌、平静而快乐的日子,但我们无可否认,在一些规模不大、管理不规范的企业,还有像阿月这样的打工嫂存在。要解决她们的问题,我想有两个措施,一是她们所在的工厂以及工会应经常举行各种有益身心的活动,让她们的苦恼在这些活动中得以排解,也为她们的生活增添一点乐趣;
二是有关部门要多关心她们的身心健康,让她们有带薪休假的待遇,让她们多一些与家人团聚的机会。如果阿月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对她们的身心,对社会,都可能产生十分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