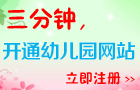我们常会惊异于儿童的提问(往往都是深刻的哲学问题),常会被儿童的纯情所感染(那么富于同情心!),常会为儿童憨态可掬的表现(那么美!)发出会心的微笑,有时候也会被他们在灾难面前所表现出的坚韧和幽默所震惊。
这是因为,我们从他们身上还可以依稀体验到日常生活中所蕴涵的令人惊异的美和诗意。童年之所以美好,是因为那时候的人有最纯净的感官,孩子是天生的艺术家,他们的感官尚未受功利的污染,尚未被岁月钝化。在他们眼里,世界的每一天都是新奇的,样样事物都罩着神秘的色彩。作家帕乌斯托夫斯基在其作品《金蔷薇》中说,童年时代的太阳要炽热得多,草要茂盛得多,雨要大得多,天空的颜色要深得多,周围的人要有趣得多。孩子好奇的目光把世界照耀得无往而不美。然后是少年时代,情心初萌,醉意荡漾,沉浸于一种微妙的心态,觉得每个萍水相逢的少女都那么美丽。那是一个人人都曾写诗的年龄(我们不是也有这样的时刻?)。“诗意地理解生活,理解我们周围的一切——是我们从童年时代得到的最可贵的礼物。要是一个人在成年之后的漫长的冷静岁月中,没有丢失这件礼物,那么他就是个诗人或作家。”可惜的是,多数人丢失了这件礼物。也许这是不可避免的,匆忙的实际生活迫使我们成年人把事物简化、图式化,无暇感受事物的种种细微差别。概念取代了感觉,心机取代了好奇,私利取代了同情和爱,我们很少看、听和体验生活中的诗意。当年伦敦居民为了谋生而匆匆走过街头时,哪有闲心去仔细观察街上雾的颜色?谁不知道雾是灰色的!直到莫奈到伦敦把雾画成了紫红色的,伦敦人才始而愤怒,继而吃惊地发现,莫奈是对的,他还葆有赤子之心,人们称他为“伦敦雾的创造者”。
诗人荷尔德林在谈到美和神性时说:完美的自然必然生活在还没有入学的孩童心里,谁若不曾是完美的儿童,也就很难长成完美的男子汉。因此他一再渴求人们:从摇篮时代起就不要去干扰孩子吧!不要把孩子从他本质的紧密的蓓蕾中驱赶出来吧!不要把他从童年的小屋里驱赶出来吧!既不要撒手不管,使他与你们产生隔阂,也不要插手太多,以致让他都感觉不到他自己的力量,只有这样,他才会成人。人一旦成其为人,也就是神,而他一旦成了神,他就是美的。诗人在这里恳求我们要认真呵护人的童年。童话大师安徒生深谙保护孩子童年的重要意义。一天,他在树林里散步,看到那里长着许多蘑菇,便设法在每一只蘑菇下边藏了一件小食品或小玩意儿。次日清早,他带着守林人的七岁女儿走进这片树林。当孩子在蘑菇底下发现这些意想不到的小礼物时眼睛里燃起了难以形容的惊喜。安徒生告诉她,这些东西是地神藏在那里的。一个耳闻此事的神父愤怒地指责他“您欺骗了天真的孩子!”安徒生答道:“不,这不是欺骗,她会终生记住这件事。我可以向你担保,她的心决不会像那些没有经历过这则童话的人那样容易变得冷酷无情。”确实,对美敏感的人往往比较有人情味,在这方面迟钝的人则性格显得枯燥,而且心肠多半容易走向冷酷。民族也是如此,爱美的、懂得欣赏美的民族天然倾向自由和宽容,厌恶教条和专制。荷尔德林认为,比之地球上其他任何民族,雅典娜的子民在任何方面都更加不受干扰,更加免受强制的影响成长起来了。马克思在阐释希腊史诗的永久魅力时说:成熟的作品产生于未成熟的社会之中并不奇怪,因为赋予史诗以永久魅力的不是社会,而是人,是带着儿童天性的人。这种本真本然的人,这种带着原始诗意的生命,便是美感的源泉,便是使我们享受不尽的“永久魅力”的秘密。
相对“雅典娜的子民”,马克思说:中国文明是早熟的儿童,希腊文明是正常的儿童。不知今天的中国人是否承认这个判断。不过有一个现象实在令我难以释怀。这就是今天中国的孩子大都被剥夺了童年,一句“决不能输在起跑线上”,让儿童早上7:30(或更早)就端坐教室,晚上10点往往才能上床睡觉,休息日还要上补习班。他们实在比成年人还辛苦!当今,似乎一切都要从是否具有商业价值的方面加以考量,而具有商业价值的事物都被迫加速发育,提前成熟,尽可能快地将自己奉献给市场:我们吃着早熟的水果、蔬菜、粮食,看着早熟的明星的表演,阅读着早熟的作者写下的文字,祝愿自己的下一代在早熟者的行列中名列前茅。也许再过若干年后,人世间的万物都将不再拥有童年。这种急功近利的时代逻辑对于儿童的心灵的扭曲是非常可怕的。一个人能“一生下来就紧张地准备考试、准备求生存的技能吗”?不可能!我们说儿童是天真的,就是因为他们还不具有功利之心,他们属于游戏并且在游戏中获得快乐,如果一个儿童早早地具有了功利之心,那么他肯定不是在顺应本性生长,而是被成人的筹划所扭曲,“在物质的灿烂灯光下,人类的童年在缩短”。
20世纪的作家冰心曾呼唤“孩子救救我!”这个命题意味着我们这些成年人拯救自我之路就是返回孩子状态———拒绝世故、拒绝心机、拒绝名利诱惑的状态。这与老子的“复归于婴儿”与“复归于朴”的意思相通,返回童心就是返回生命的自由与尊严。可是,今天我们不仅不反省自己“因成年而变得丑陋”,还将丑陋的“筹划”延伸到儿童。每当看到孩子沉重的书包和疲倦的眼神,都令我心痛,今天首要的任务是保护孩子的童年,因此鲁迅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唤显得特别切中时弊。
英国思想家柏林说:“活着多么好。”尽管人生有难以释肩的重负,但有许多美好的瞬间,它们足以支撑繁重的人生。而捕捉这瞬间之美需要有一颗赤子之心,我们还有这颗心吗?
附:本文写于“5·12”地震灾难之前,我的心在为死亡的孩子流泪,更为活着的孩子的未来而担心。谨以此文献给地震后的这个儿童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