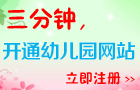一、政策目标,及其与政党政治、阶级关系、家庭型态、性别意识之相关性
北欧五国中,公共托育服务发展最早、提供量最大的是丹麦;瑞典后来居上,具有最完善的公共托育服务网;挪威和芬兰公共托育服务较为不足,但晚近挪威政府规划针对所有有托育意愿之父母提供学前公共托育服务,并大量增加课后托育服务。以上四国的托育制度大致符合一般所谓的「北欧模式」社会福利服务。
丹麦和瑞典是北欧模式托育制度的代表,其政策目标有三:一为给予孩童平等普及的托育,二为支持父母(尤其是母亲)就业,三为实现男女平等。形塑这三项政策目标的最重要因素,无疑是北欧国家/社会的基本价值:平等精神。「平等」的信念基本上是对劳工阶层以及女性友善的价值,因此其国家制度能够优先顾及劳工(受薪者)阶层孩童照顾与教育之需求、劳工(受薪者)兼顾工作与家庭的需求,以及女性要求平等的呼声。
丹麦和瑞典的托育「福利」,有着另一个面向,那是其余地区研究者容易忽视的面向,而那便是其为国家积极劳动政策之一环。其做法为:规定只有在父母双方(或单亲)参与劳动的的状况下,其小孩才有享受托育福利服务的权利。这项规定具有相当完善的配套措施,包括为期相当长的有薪育婴假、条件相当宽松的亲职假(用以照顾病童)、完善的再就业训练及辅导(失业者只要进入此训辅计划即能让子女继续享受公共托育服务)等等。
也就是说,丹麦和瑞典的托育制度不是单纯的福利政策,而是福利政策与劳动政策的结合体,这使得这两国的托育福利服务同时具有「红萝卜」和「棍子」的双面特质。从这项特质我们可以看到北欧模式福利国家的务实本质,他们将「享受福利」和「工作/纳税」两件事紧紧地绑在一起,让两者互相支撑,相辅相成。就托育而言,这意味着传统家庭与保守意识形态下的「养家活口的男人与家庭主妇的相互责任(他负责赚钱养家,她负责家务育儿)」,已为「成年公民与国家的相互责任(成年公民参与劳动,国家于工作时间为他们育儿)」所取代。当我们思考效法北欧制度时,必须特别注意这项设计,因为这是立意甚高的北欧模式的存活诀窍。
北欧模式福利服务制度还有一个我们不应忽视的特点,那便是其服务对象涵盖中产阶级。一般国家仅仅针对弱势群落提供免费或高额补助的托育或赡养福利服务,而将中上阶层所需的照顾服务委诸市场和个别家庭,但是,北欧模式却将中产阶级纳入服务范围。这是很重要的设计,充分反映瑞典等国左倾执政党之结盟对象从劳工扩大到整个受薪阶层,乃至于涵盖中产阶级的历史发展。
这样的发展带给北欧福利服务制度以及整体社会多面向的正面效应,包括:(一)中上阶层加入共享体系,将其财力(税金)、脑力投入此体系,大大提升此体系的可近性与服务水平,形成良性循环,而得以使其存活率大为增加,同时另一方面中产阶级也因为满意于此福利服务体系,而愿意交税、参与其(民主协商模式之)运作,以致于从来不曾有过抗税的危机;(二)中下阶层共享此水平高、可近性高、大幅度以税金支付之托育服务(以及其它类似之福利),其生活水平得以大大提高,产生「去普罗化」、「中产阶级化」的效果;(三)照顾福利服务的跨阶级共享,意味着实质生活的大幅度跨阶级特质,如此形塑活生生的社会团结,或「生命共同体」,具有减少冲突,增进合作,将社会弊害降至最低,将社会乐利增至最大的作用,国家、社会以及个人同蒙其利,如此,北欧模式借着资源的参与式民主模式集体运用,稳定且普遍达成了功利主义借着「自由」「放任」以企求却不容易达成的个人与整体社会的最大利益;(四)高质量的普及福利措施,尤其是托育措施,具有长期稳定国民(劳动力)素质的作用,有助于提升社会水平和国家经贸竞争力。设计妥善的普及福利制度,尤其是1960年代以后大幅度发展的普及照顾福利服务,可以说是天然条件不佳、大幅度依赖国际贸易的北欧各国得以长保社会团结与安宁、高质量人口(劳动力)素质及高度经济繁荣的诀窍。除此之外,良好的托育制度无疑也是提高女性就业率与生育率的重要因素,使得北欧各国享有先进国家中甚高的妇女就业率与生育率。如此,北欧模式托育与其它福利措施达成了妇女权益与生育率同时提升的奇妙效果。
就照顾服务而言,北欧模式的发展是从社会救助到社会福利服务的转化。造成此项转化的力量主要有三,其一为社会民主政党,其二为劳工或工会,其三为女性。劳工和女性不像资产阶级男性(后者正是现代国家法律所着重保障的家户长、家庭财产所有者)有自求多福的能力,前者的权益需要靠集体的力量来保障,因此他们主张国家应有所作为,政府应做较多的介入。经由自觉的结合,他们群起以选票支持以其权益为念的社会民主政党或劳工政党,使之长期执政,将劳工和女性需求之满足转化为国家政策与政府施政的重点。就照顾福利服务(尤其是托育)而言,可想而知,女性的因素尤其关键。这说明了何以北欧照顾福利服务的大规模发展,是跟兴起于1970年代的第二波妇运同步进行的。劳工和工会希望国家介入市场,女性希望国家介入家庭事务,而且,这两种人都希望把家务工作转化为有酬工作,以为(女性)劳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这两种人联合支持社会民主政党,得以突破基督教政党和农民政党的传统家庭价值,以及右派政党的自由市场万能论和自愿主义(即主张社会服务和社会救助应由自愿组织去做)。
丹麦是公共托育的前锋,从1950年代起就开始拓展托育福利服务;晚近去中央的意识形态兴起后,丹麦也在这一方面带领潮流,将照顾福利服务推向「地方自治」与「税金支付」两相结合的方向。民间组织在丹麦的机构式托育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但这跟北欧模式并不冲突,一来因为经费大幅度仍是来自于税金(以及少部分自付额,完全没有营利),二来因为它显示的是民间社会跟公部门的密切连结,因此跟许多国家的「私化」、将托育责任归诸营利市场、家庭、自愿团体的做法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
瑞典是北欧模式社会福利服务的典范,它于1960年代起大规模投资于公共托育措施。以其公部门所扮演的中心角色、其数量庞大的公共托育服务,以及对于质量和普及性的注重而言,瑞典展现了最典型的北欧模式。1991-1994年间右倾政党的执政虽然导致福利制度的些微右转,但是,自从1994年社民党重回执政宝座之后,右转的趋势已经停止。
芬兰的照顾服务体系也是普及式且高度依赖公部门的,但是,近年其托育提供量却不进反退,成为北欧五国中的最后一名。这是因为1980年代之后农民政党掌政,删减托育服务经费,挪作家庭照顾津贴所致。(瑞典的右倾执政党于1994年推动类似的转变,但该政策为该年稍后夺回执政宝座的社民党所终止。由此我们可知,家庭照顾津贴跟公共托育服务分属相反的政治/社会/家庭/性别意识形态,前者是有余裕让已婚女性不工作待在家中从事照顾劳务之中上阶层、传统家庭价值、传统刻板性别角色观、右倾政党的主张,而后者则是劳动阶层、双薪家庭、两性平等价值观、左倾政党的表现。)
挪威的例子让我们见识另一个层次的问题,那便是托育服务的提供者(地方政府、民间非营利组织、托育专业者)跟使用者(父母)之间的利益冲突,以及前者对于决策和立法过程的垄断。1969年的中间偏右执政联盟政府指派七名男性和五名女性组成托育政策研议委员会,此委员会于其结论报告中提出两个要点:(一)地方政府必须被赋予规划及提供托育服务之责,中央政府并应针对托育服务而大幅度提高对于地方政府的拨款;(二)家庭托育(保姆)应被纳入由政府管辖。这样的建议,简而言之,意味着托育服务的公共化与普及化。可惜的是,这份立意甚佳的建议并没有成为其后立法与施政的蓝图。
其后执政的工党政府着手进行立法的准备,邀请各部会、地方政府、劳工组织、雇主组织、参与托育服务的民间组织和专业者、两性平等委员会和一些妇女组织,针对托育政策提出建言。被赋予提供服务之责的地方政府反应最为热烈,其所提出的意见占建言总量的一半,而可想而知,由于其传统家庭价值与刻板性别角色观(一般而言,基层社会是传统刻板性别角色观的堡垒),以及出于不愿意负担庞大公共托育服务费用的心态,地方政府一概表示反对硬性规定由地方政府负责提供托育服务。工会(1970年代男性主导的工会)看到的是托育工作人员的权益,而不是广大的工会成员作为父母和托育服务消费者的权益;参与托育服务的民间组织和专业者在乎的是政府的补助和专业水平;至于需要托育服务的家庭和父母,尤其是欠缺组织基础的学龄前儿童父母,则未留下任何发言纪录。根据这些建言,工党政府草拟法案,其后国会于1975年照案通过这份「托育法案」。
如此,供方(地方政府、民间组织和专业者)成为挪威「托育法案」的赢家。地方政府有权决定如何提供以及提供多少托育服务,却被免除了硬性的责任;从事托育服务的民间组织得到政府补助的营运费用和低利贷款;幼教老师则成功地护卫其专业垄断,排除保姆,而保住了对于政府补助的寡占。输了的则是父母和儿童,他们或者因为提供不均匀、量不足而不能享受机构托育,或者因为幼教专业者倾向于提供半日托育而必须在数个托育者/处所之间奔波,同时因此损失对于国家补助的享受及国家负责家庭托育所能增进的质量。输了的是女性,就业率在世界上仅次于瑞典、丹麦、芬兰三国的挪威女性,必须靠自己奋斗兼顾工作与育儿。输了的还有为数众多的保姆,她们因为地方政府的省事心态,和营运托育机构的民间组织及幼教专业者的垄断,而失去政府纳管所能带来的补助/协助和工作能力/质量的提升。
挪威的例子显示的是「地方自治」、「自愿主义」与「专业」打败了普及照顾福利,基层社会的传统家庭与性别意识形态凌驾左倾执政党的平等意识形态。不过,Sipila et al.指出,挪威近年的发展已经突破Leira的前述分析。表二显示,于1987年之后,挪威政府开始大量发展机构托育,同时全日托的比例也逐年大幅度增加;跟底下冰岛的例子相比,可知左倾的平等意识较强的挪威,还是比右倾的冰岛更有转圜的潜力,能够大幅度转向,由保守家庭意识与传统性别角色观转为相当彻底的两性平等制度(详见底下各节)。
冰岛的托育可以说是欧陆型态和北欧模式的(不良)结合,其特色为:(一)幼教专业取向,侧重教育功能及幼教跟国小的衔接,而忽略照顾功能;(二)多数公办托育服务每日仅提供4-6小时托育,小孩必须奔波于数个托育场所之间;(三)提供量不足,而且公办托育以弱势家庭为优先,以致一般父母不易得到服务,譬如,首都雷克雅维克的公办全日托只对一般家庭开放百分之二十的名额,这跟「中产阶级与弱势家庭共享平等普及的托育福利服务」的北欧模式大异其趣。
这是因为冰岛不像北欧其余国家(尤其是瑞典、丹麦、挪威三国)那样长年由左倾政党执政。在冰岛,从二次战后至今,右倾的独立党一直是执政联盟的成员。不仅于此,冰岛人比较注重家庭的育儿功能与托育质量的提升,因而陷入右派路线典型矛盾:反对国家介入家庭、干涉市场的右派意识型态主导之下,国家/社会对于托育投资必然不足(参见表六),如此,提升幼教质量的期待成为空想。Broddadottir et al.指出,Leira对于挪威的分析也适用于冰岛。Leira说,丹麦和瑞典将托育政策和劳动政策、人口政策绑在一起考虑,而挪威则否。冰岛和挪威一样,将托育单独考虑,侧重幼教功能,导致「法律明文规定的幼儿教育权无法普及实现」,并显示「政府的托育措施跟时代需求脱节」。(晚近挪威托育政策已经大幅度转向,详见底下分析。)
二、教保目标与内涵界定
前面第一节对于北欧五国托育制度异同之探讨,相当意外地触及了台湾当今所面临的托教分合问题的核心关键,让我们恍然大悟:原来托教分合牵涉着的是阶级利益或阶级意识,以及性别角色意识。冰岛长年由右倾政党执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只有三个任期为左倾政党执政),人民较注重家庭的育儿功能,想要使用学前机构的家长偏重教育功能,这些特点使冰岛的公共托育服务具有政府资源投注不多、提供量不足、提供时间无法配合父母工作之需、残补色彩浓厚(全日托大部份由弱势家庭使用)、中产阶级及双薪家庭得不到全日托服务只得求助营利业界等等特色。挪威由于传统家庭价值浓厚,其托育政策也有类似的缺失,但是,在左倾政治意识与性别平等意识的引导之下,晚近挪威已有大幅度的修正,向瑞典和丹麦看齐。而芬兰在1980年代农民政党执政之后,导致托育政策的反向发展,以致提供量萎缩。
就目前的情况而言,瑞典、丹麦、挪威三国的托育政策,尤其是瑞典和丹麦,堪称「北欧模式」的典型代表,其特点为公共提供、平等普及、充分配合父母的工作需要。跟随着这个模式的发展,「托儿所跟幼儿园的旧有区分被取消了,教育和照顾被规划融合在同一个托育体系里,取代战前的阶级区隔的托育制度」。两种制度的过渡,一直到今天都还在进行。譬如,瑞典在1970年代末期起大量增设(全日制,收托1-6岁小孩)托儿所之后,(半日制,有寒暑假,主要收托4-6岁儿童)幼儿园所提供的服务量便持续萎缩,于1995年收托儿童仅占当年公共托育服务(托儿所、幼儿园、保姆)注册小孩的12%,而且其中大部份为前来享受免费托育的6岁儿童,而这些6岁儿童往往同时使用家庭托育或托儿所,以便能跟父母工作时间衔接。丹麦也保有幼儿园和托儿所的二分,但前者收托比例相当低;挪威托儿所收托的则以幼儿园年纪(3岁以上)儿童为主,而且,要到1990年代,全日托的人数才超过非全日托(4-6小时)的人数。
为了因应父母就业的需要,瑞典和丹麦也针对国小学童大规模提供课后托育。挪威则于晚近开始于学校场所提供课后托育;瑞典近年则把课后托育中心跟学校融合,以减少政府开销,并提高学校教育与课后托育的连贯性。由此我们可知,对于托育措施之教育功能的偏重,是跟单薪高收入之中上阶层所注重之家庭育儿功能、传统家庭价值、传统刻板性别角色并存的;而对于劳动阶层与女性兼顾工作与育儿之需求的考虑,则会导向托育措施之教育与照顾功能之并重。
兹以瑞典为例。瑞典政府责成卫生与福利部组成委员会,负责研议学前及课后托育的内涵及目标。该委员会于1987年发布成果报告,将托育工作做如下的定位:
□ 托育必须跟家庭相连,而且,跟父母的密切合作是重要的。
□ 儿童的学习是随时随地都在进行的,因此,照顾也是整体教育的一环。
□ 教学活动应从儿童本身的经验和先前的知识出发。
□ 扥育服务必须引领小孩对于自然、文化、社会有整体的认识,并且协助小孩感受万物共存互动的整体性。因此必须采取主题式的方法,引导小孩针对特定的主题以各种方式探讨、学习之,经由阅读、听故事、角色扮演、舞蹈、肢体运动及其它活动,开发儿童对于官能和心智能力的运用。
□ 应注重团体活动对于儿童学习与发展的重要性。
我们发现,这项定位着重:(一)照顾和教育的不可分;(二)儿童教育应注重传递自然、文化、社会的整体性,以及所有个人乃至万物的共存互动。这样的定位显示出跨阶级/性别共存合作的意识,以及生态保育的意识,同时充分顾及劳动阶层工作和育儿的需求。此外,将照顾视为教育之一环,以及将万物共存的整体性视为儿童学习的重心,这样的理念与做法也可能比将照顾与教育二分、专注于个别儿童的心智发展的传统欧美幼教主流更为接近儿童生活与学习的实际情况,因此可能反而比较能够有效帮助儿童学习成为有广博且有用的知识、有良好的道德与人格结构的人。或许我们可以说,北欧模式扥育措施的普及共享本身即能发挥很好的教育功用,有助于心胸与视野的开阔。
相对而言,较为右倾的冰岛强调的是扥育机构的教育功能,其于1973年通过的扥育法案将扥育机构划归文化与教育部管辖;1981年修法时规定,文化与教育部应会同合格幼教专业者共同规划扥教机构专业工作之目标与细节。其于1991年进行的扥育法案修正,进一步将「托儿所」(“day care institution”)改名为「游戏学校」(“play school”)。这项概念变革显示的是「游戏学校被视为教育机构或学校,是学校系统的第一层」;而「游戏学校」的名称标明在此透过游戏进行的是指导儿童学习与发展的专业化工作(professional work)。但是,讽刺的是,阶级区隔与教育、照顾的二分,导致全日扥服务发展不足,使得大量兴起的中产阶级双薪家庭反而无法享受。右倾扥育政策路线的自相矛盾与不符时代需求,于此可见一斑。
瑞典于1996年起将扥育的主管机关从卫生与福利部挪至教育部,但其立意与冰岛大异其趣。冰岛朝向将学前扥育纳入正式教育体系的方向发展,而瑞典的改制,用意则在于「将学前机构、学校及课后扥育融入为终身学习的一部分」;瑞典强调的是不受正式教育体系局限、持续不断、全方位的终身学习(我们必须注意,照顾亦为此终身学习或教育活动的一环,正如前面所说明过的),并将其教育部的视野及管辖内涵往这个方向推展,这可以说是全世界最进步的国家教育/学习政策。
由此可知,教育、照顾功能的融合或偏重一方,会影响政府角色与行政体系。这将于下一节进一步说明。
三、政府角色、民间角色与行政体系
先从「北欧模式」最边缘的冰岛说起。相对于其余北欧国家而言,较为右倾的冰岛政府和社会偏重家庭的育儿功能与扥育机构的教育功能(而非照顾功能),因此,很自然地,其于1973年通过的扥育法案将扥育机构划归文化与教育部管辖;1991年修法将「扥育机构」改称「游戏学校」,对于教育功能的偏重益加明显。保姆于1992年纳入管制,划归社会事务部管辖。由此可见机构扥育与家庭扥育分别偏重教育与照顾的区隔。从1994年起,扥育机构的督管责任由文化与教育部挪至地方政府,于其下设「游戏学校委员会」管辖之。
冰岛机构扥育侧重教育、轻忽照顾的倾向,及其晚近地方化的走向,两相结合(即阶级区隔+传统家庭与性别意识+地方化与层级矮化),导致国家/社会对于新兴双薪家庭需求的忽视与无以因应。这跟瑞典、丹麦的扥育政策(跨阶级共享+性别平等意识+先中央化、规格化、两性平等化之后再进行地方自治化)及其成效形成很大的对比。
接下去先让我们来看居中的挪威的情形。比诸瑞典、丹麦、芬兰而言,挪威(至少在较早期)在家庭价值方面是比较保守的。它不同于其余三国,而专设「儿童与家庭事务部」负责管辖有关儿童与家庭之事务,显示挪威人认为儿童属于家庭的保守心态。
可想而知,在挪威,扥育机构既不归社福部门也不归教育部门管辖,而是隶属于儿童与家庭事务部。这样的设计预设了育儿为家庭责任的前提,因此,非全日扥、三岁以上收扥成为机构扥育的主要设计,而家庭育儿则被排除在政府管辖或负责的范围之外。
这样的设计于1990年前后受到学界及妇运界的猛烈批评,以及新兴双薪家庭需求的强大撞击。幸亏挪威不像冰岛。冰岛面临右派意识与传统家庭价值双重的绑缚;而挪威则是深具阶级平等意识的国家,所需破除的,仅有传统家庭意识与刻板性别角色而已,而后者于第二波妇运展开后已逐渐被意识为社会平等的主要绊脚石之一。以追求平等为要务的挪威政府与人民于是带着「觉今是而昨非」的劲儿,并挟其充裕的国富资源,大幅度增加全日扥福利服务的提供(见附录表二),甚至制定政策,预计于2000年达成对于所有有需要之家庭提供机构扥育服务之目标,同时大幅增加于学校场所提供之学童课后扥育。
在扥育政策上具有前锋身份的丹麦主张儿童事务具有跨部会性质,因此于1987年成立涵盖15个部会的「跨部会儿童委员会」,而以社会事务部担任主席之职。丹麦法律规定,所有有需要的小孩都应享受公共扥育服务,而提供此项服务之责则归于地方政府。根据1997年的资料,地方政府直接设置的扥育机构占所有扥育机构的三分之二,其余三分之一由民间非营利组织或团体(主要是父母互助团体)在得到地方政府之同意之情况下经营;但是,无论经费来源或扥育内涵,两者并无二致。除了机构扥育之外,还有受地方政府督导的保姆,以收扥零至二岁幼儿为主。有需要扥育的父母向地方政府(乡镇公所)提出申请,后者会依据需求程度加以评估,并给予安排;如果没有名额,小孩就会被列入等待名单。根据法律,父母被赋予参与扥育机构的正式管道,可以组成家长委员会。家长委员会由家长代表组成,工作人员也派代表参加,其职责为:为该扥育机构订定教学等活动原则、制定预算及财务管理原则、选派代表参加地方政府的扥育委员会(此乡镇扥育委员会负责幼扥师资之甄选、地方预算之分配等事务)。
堪称全世界最注重扥育(以及长期照护)福利服务的瑞典,于1996年起将扥育的主管机关从卫生与福利部挪至教育部,其用意在于「将学前机构、学校及课后扥育融合为终身学习的一部分」。我们必须注意,这项举措强调的不是扥育工作的教育「专业」,而是不受正式教育体系局限、持续不断、全方位的终身学习。除此之外,我们也可以合理推测,改制的另一个因素,应是部会权责份量的调整。瑞典于1993年起将牵涉长期照护的事务,大幅度由县政府的健康与医疗事务部门挪至乡镇公所的社福事务部门;衡诸瑞典之为全世界高龄化程度最高、对老人的照顾福利服务最完善之事实,可知前述调整会大量增加乡镇公所社福事务部门的负担。很可能是出于进一步调整之需,扥育事务被从许多乡镇公所的社福部门独立出来,单独运作,并进一步将其中央主管机关由卫生与福利部挪至教育部。这两项改制使得长期照护和终身学习这两项瑞典政府与人民素所侧重的事务达成了持续性与完整性的建立。
瑞典扥育的行政体系中,主管的中央部会(先前的卫生与福利部与现制的教育部)负责对于托育计划、地方政府管辖人员及扥育工作人员的指导手册、师资培训体系、促进研发方案之整体规划,以及部分经费的筹措。乡镇公所先前的社会福利委员会、现制的扥育委员会负责扥育措施的设立或扩张事宜,并负责督导各项扥育措施达成既定扥育政策目标(Broberg and Hwang 1991: 83-84)。至于保姆,乡镇公所聘有保姆督导负责评估、甄选、督导保姆,提供咨询与支持,配置受托小孩,并促成或举办保姆或幼儿的活动。
在瑞典,地方政府可以对达到合格质量的平价民营扥育机构核发补助。这样的学前扥育机构于1995年收扥了12%的受扥学龄前儿童,而此类民营课后托育中心则收扥5%的受扥学童;民营托育机构中,最多的类型为父母合作社形式,约占半数,次多的是民间组织或公司所经营者。瑞典扥育措施的民营化,甚至营利化(比例极小),是1990年代初期执政的右倾联盟所推动的,于1994年社民党重回执政宝座之后,其中营利化的倾向可以说已经停止。至于委由民间非营利组织以参与式民主方式经营的部分,则跟随着「去中央化」、「去规格化」与「政府与民间社会合作」的趋势而发展,类似于丹麦的情况。
关于经费,丹麦、瑞典、挪威、芬兰都采取融合税金支付、部分自付额与对弱势儿童的补助之方式。1987年的数据显示,瑞典学前扥育(机构及保姆)福利服务经费使用者自付额为10.8%,丹麦为18.3%,挪威学前(机构)扥育福利服务使用者自付16.3%,但多于一个小孩使用之家庭可以得到大幅度的减免,以便让所有小孩都能享受。到1990年代中期,丹麦的使用者自付额提高为30%;近年瑞典自付额也大幅提高。由此可见这些国家对于自付额采取的是务实的浮动比例原则,因应国库的盈缺而随时做调整。在丹麦和瑞典两国,自付额,包括给予保姆或所谓「民营」托育机构的自付额,都是由父母付给地方政府。
在丹麦和晚近的瑞典机构化扥育中,民间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但是,我们必须特别注意的是,这些民营扥育机构(除了瑞典于1990年代初期由右倾执政联盟所催生的为数极少的营利化民营扥育机构之外)接受跟公营扥育机构同样比例的政府补助,而且也一样以参与式民主方式营运,并派代表参加地方政府之参与式民主模式之扥育委员会,因此,其定位应是public,而非private,跟一般所谓的「私化」大异其趣,我们顶多只能以「公私融合」或「政府与民间社会的合作」形容之。
(编辑:l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