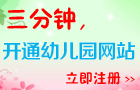在儿童教育中,何谓善?何谓恶?换言之,区分善、恶的标准是什么?美国学者杜威关于经验的相关论述也许会给我们一些启示。“经验”是杜威教育理论中的一个核心概念。他认为:“经验包含一个主动的因素和一个被动的因素,这两个因素以特有形式结合着……在主动的方面,经验就是承受结果。我们对事物有所作为,然后它回过来对我们有所影响,这就是一种特殊的结合。经验的这两个方面的联结,可以测定经验的效果和价值。”这里的“影响”一词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对个体当前的影响;二是指对个体以后的影响。我们说“影响”的性质是由后者(即对个体以后的影响)决定的。例如,一个小孩把手伸进热水里,这本身不是经验。只有当这一行为和他所遭受的痛苦联系起来时才是其成为了一种经验。这一经验对个体的影响包括两方面:一是个体当时感到痛苦;二是个体以后可能会因此而惧怕探索新奇的事物,或者在做事时会比较谨慎。我们可以根据这一经验对个体以后的影响的性质来判断这一经验的性质。也就是说,如果由于这一经验而使其在以后的时光中惧怕探索新奇事物,则这一经验就是消极的;如果由于这一经验而使其在以后探索事物或做事时比较谨慎,则这一经验就是积极的。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杜威在《经验与教育》中明确指出:“经验的价值只能由它所推动的方向来评判。”我们认为,儿童教育中的善与恶主要是以是否有利于儿童发展作为衡量标准的。也就是说,有利于儿童发展的就是善的,反之,则是恶的。由此观之,某一特定教育行为的善恶是因人因时而异的,这也正是儿童教育中善恶的辩证性之所在。
在分析儿童教育中的善恶问题时要注意克服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用一种生态意识进行分析。具体说来,就是要摒弃那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认为感性与理性、善与恶等之间并非绝对对立,而是可以对话,并且是一种共生、互补的关系。当我们运用这种观念分析儿童教育中善恶问题时会发现,问题的关键不是在儿童教育中区分出哪些是善的,哪些是恶的,而是将儿童教育本身视为一个生态,其中的各个要素(如教师、儿童家长及其各种行为等)视为这个生态系统的有机要素,在它们之间建立良好的生态关系,而非你死我活的关系。
正是由于儿童教育中善恶的这种辩证性,所以有些在一般人看来是善的东西(如过早地学习钢琴、绘画等,以免自己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对于特定年龄阶段的特定儿童而言则可能是恶的。当前很多教育现象(如零岁方案、超前识字等)无不说明了这一点,与此同时,有一些在一般人看来是恶的东西(如玩杀人游戏、祭祀或葬礼游戏等)对于特定年龄阶段的特定儿童而言则可能是善的。著名的和平主义者罗素曾津津乐道地讲述过了的儿子玩过一个青髯公杀妻的游戏。在此游戏中,他的儿扮演青髯公,将其六个妻子都“残忍”地杀掉了,在此过程中还出现过砍下女人头颅的惨景。看到这里,也许很多人会对罗素的“宽容”感到惊讶,并提出异议,罗素也早已预料到了这一点,他在《教育论》中指出:“作为一个和平主义者。你怎能允许你那天真的儿子以杀人之念为乐见?你怎能为那种源于人类必须弃绝的野蛮天性的快乐作辩护呢?想必读者都有这许多疑问。”罗素是如何为自己辩护的呢?他指出:“教育在于培养本能,而不是掏本能。人的本能是很模糊的,可以用很方法满足……因此品性教育的秘廖在于向人们提供那类能使他们有益地利用本能的技能。在孩子提时代由装扮青髯公所粗糙满足的权力本能,以后便可通过科学发明、艺术创作、培养教育杰出儿童或其他任何有益的活动来获得高尚的满足。如果某人只懂得如何打仗,他的权力欲就会使他喜欢作战。但若他还有别的技能,他就会通过别的方式来获得满足。然而,如果他的权力欲在儿童时期就被扼杀于萌芽状态,他将会变得无精打采,既不做好事,也不做坏事。这种弱者的善不是世界所需要的,也不是我们应当努力使孩子具备的……如果你能使他们获得高尚满足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就不必担心他们会停留在这个水平上。我小时候很喜欢翻跟头。
现在我从不这样做……同样,喜欢装扮青髯公的儿童将来也会改变这种嗜好,从而学习以其他方式寻求权力。”
我国幼教领域也曾对类似的问题展开过讨论,如一些幼教工作者曾就儿童玩“出格游戏”进行过讨论。有一篇文章中特别提到了这样一个游戏案例:在某幼儿园,一天,有些幼儿在玩“娃娃家”游戏时,经某一幼儿提议,他们玩起了“死人”游戏。一开始,教师没有注意到,直到第三天,教师才发现了这一现象。这位教师认为这种游戏不好,因为它反映的是封建迷信。但幼儿又玩得非常投入。该怎么办呢?后来,这一教师假装医生,然后对正在玩“死人”游戏的幼儿说这个娃娃其实没有死,只是生病了,然后和幼儿一起将娃娃送到了“医院”,并声称该娃娃需要住院治疗。后来,这些幼儿很不情愿地离去了。但是,第二天到了游戏时间时,幼儿又来跟教师要娃娃。此时,教师仍然以医生的口吻告诉幼儿说:娃娃的病还没有好,需要继续住院治疗,不能出院。幼儿只好回去了。许多幼教工作者认为,当教师看到幼儿玩类似的游戏时应当给予一定干预。看到这个案例后,我也曾困惑过:教师看到幼儿玩类似的“出格游戏”时应该怎么办?是听之任之?还是加以制止?抑或其他?若允许他们玩类似诉“出格游戏”,他们会不会真的成为封建迷信者?会不会长大后还热衷于此?看了罗素的《教育论》后,我茅塞顿开:他们之所以玩类似的游戏,是因为他们对生和死等自然现象充满了好奇,是满足此方面好奇心的一种方式,并且仅仅是其中的一种方式而已。当他们篚后获得了其他技能时,自然会不再热衷于这种方式,而是寻求其他的方式满足这方面的好奇心。因此,我们完全没有必要担心,担心他们长大后会真的不务正业。这是杞人忧天。看了这个案例后,又促使我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即儿童是如何变恶的?是否是成人使儿童变恶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成人是否应当对儿童变恶负有一定的责任呢?在此案例中,这位教师之所以对幼儿的游戏进行干预,是因为她认为这种游戏不好,之所以不好,原因很简单,因为这种游戏反映的是封建迷信。看到这里,我很困惑:幼儿在玩这种游戏的过程中有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呢?我想,他们可能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只是觉得这样好玩。因此,当我们看到幼儿玩类似的游戏时,决不能给他们扣大帽子,说他们反科学,搞迷信活动。令人非常欣慰同时也非常幸运的是,在这一案例中,教师并没有将这种所谓的理由告诉他们,而只是引导他们不再玩这种游戏,虽然他们对这种游戏非常感兴趣。但在很时候却并不总是如此幸运,如当看到有的儿童在“残忍”地将蚯蚓撕成几段时,有些在人会感到非常震惊:这些孩子怎么会如此残忍?我们怎能容忍他们这样做?更为不幸地是,他们有的会大声训斥这些“残忍”的儿童。殊不知,他们在这样做的时候已经使儿童知道了什么残忍,并且很有可能真的如你所料。这一儿童会变得非常残忍。从这种意义上说,正是成人不恰当的教育使儿童变恶了。
总之,我们在判断儿童教育中的善、恶时一定要摆脱自我中心,要从儿童的角度出发,以是否有利于儿童发展为依据做出最终评判。惟有如此,才能够真正有利于儿童的发展,使他们真正成为一个善良的人,一个充满活力的人。这是因为:“有些东西,按成人自身的尺度,或许是应当祛除的,然而,对于儿童则不然,恰应满足之,因为这正是他以后发展为一个健全的好人、完人的基础。逆其本性,阻遏其自然需要,也就断了儿童成长所需要的‘营养’、断了儿童所欲同化、加工的材料,因而,他便会受伤、枯萎。”因此,“儿童精神世界中表现的野蛮、荒唐,被成人视为毒药、臭粪的,对于儿童的成长却可能是养料和除虫剂。臭粪固然臭虫,便它可以化腐朽为神奇,为植物提供成长的养料;毒药固然毒,但它可以以毒攻毒,可用以杀虫。我们在这里接受臭粪和毒药,是取它们的工具价值而不是视它们为目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具体处理儿童精神生活中人微言轻成长发展阶梯的恶与作为成长结果的恶。将二者区别开来,这是一个难题。”
儿童教育中善恶的辩证性使教育成为了一门最辩证的科学。对此,马卡连柯曾有过精彩的论述:“教育学是辩证法的科学,绝对不允许有教条存在。”他说,“没有十全十美的方法,也没有必定有害的方法。使用这种或那种方法的范围,可以扩大到十分普遍的程度,也可以缩小到完全否定的状态――这要看环境、时间、个人和集体的特点,要看执行者的才能和修养,要看最近期间要达到的目的,要看全部的情势如何而定。再没有比教育学更辩证的科学了……”也就是说,“教育影响的辩证性的作用是很大的,以至于任何的地方如果它的作用不受同时和它一起运用的其他一切方法的约束,就不能够设想为是好的方法……因此,个别的方法永远可以是好的方法,也可以是不好的方法,决定的因素不是方法的直接逻辑,而是被协调地组织起来的整个方法体系的逻辑和影响”。并且,“方法体系本身永远不应当是死的东西,不应当是凝固的东西,它应当永远变化着,尤其是因为儿童在成长着……因此,任何的教育方法体系,都不可能一经确定就一劳永逸”。换言之,“最好的方法,在某些情况下,必然会成为最坏的方法”。所以我们说,教育学是最辩证的科学,绝对不允许有教条存在。也正因如此,教师在教育过程中必须要运用自己的智慧,通过分析环境、时间、儿童个人和集体的特点等,结合自身的特点选择此时此地最适合的方法,并且要不断地根据具体情况调整自己的方法。也正因如此,我们才说教无定法。唯有如此,教师才有可能在儿童教育中为善,而不为恶。